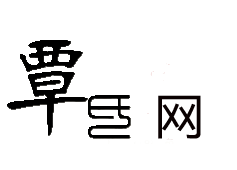
京城茶艺怪才段云松
- 4510
- 0
在北京,从三里屯酒吧到星巴克咖啡再到五福茶艺馆,穿梭在动静之间的人们在充分地享受着生活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进了茶艺馆,无论联络感情还是谈生意。坐在幽静质朴的五福茶艺馆里,品着香茗,耳边飘着若有若无的音乐,整个人都会被一种脱俗和雅气裹住。从打架斗殴到掀起京城餐饮业怀旧之风再到第一位京城茶艺人,段运松可谓一路摸爬滚打而来。那天,在福丽特中国茶城段云松那间溢满茶韵的办公室里,他细细的跟记者聊了许多。
老实说,上学时我不是个好学生,初中时,每到元旦前我就开始倒卖贺卡,我分给各年级的坏孩子每人十张贺卡,让他们到护士学校宿舍去卖,三毛钱进的卖一块,一百张就能赚七十块钱。上学时,我骑着三轮车带上五十条纱巾,等下课了就在校园里卖。初二时,爷爷去世了,父母回老家处理后事时,我就在家组织一帮孩子去卖莴笋,后来邻居告诉了我妈。当我在梦中喊着“瞧一瞧,看一看!”时,我爸过来从床底下翻出一杆秤来,他和我妈都很伤心。身为工程师和经济师的父母决不允许他们的儿子变成小贩子。看着他们的儿子整天烫着卷发,穿着喇叭裤,嘴里叼着烟卷儿,喝二锅头,交女朋友,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闲逛、打架斗殴,做小买卖,父母为此伤透了心。
放假时,我晚上在东四夜市卖油炸鹌鹑 ,白天帮着开小卖部的哥们儿卖烟,还骑着三轮车从塔院到紫竹院去进酱油、汽水。高三那年大年三十,我四点钟就起来,推着炉子、两百个碗和过桥米线到地坛庙会去卖,走了近三个小时才到,结果还让火把头发燎没了,卖了一百碗赚了九十块钱。
我知道了周末的韭菜比油菜好卖,香蕉见风就发黑。当然,这些都是从经验中得来的。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,每周六学校广播处分的名单里准有我,初三的模拟考试不及格,回家后,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躺在床上,我清楚地记得,当时,我妈站在那儿看着窗外,我知道她在哭。过了一会儿,她说了一句‘我真不知道明年的今天你能干什么!’,我一愣,深深地被刺痛了,一下子就坐了起来,我只说了一句话‘ 您放心吧!’。从那时起,我开始拼命地学习,我从全年级倒数第三名冲到了正数第十三名,考上了高中。爸妈高兴地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请了两大桌。后来,我学习又放松了,结果,大学没考上,我失学了。
总有一天有一辆车是属于我的
大学没考上,爸妈让我去他们的单位当个工人,我不去。当时,正赶上北京金朗饭店要开业需要人,凭着从朋友那儿现学的几句英语口语,我被录取了。又听说王府饭店在招人,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早晨五点就去排队抓号,还带了七八个小兄弟,让他们领七八个号,以减少竞争。结果,我靠着背熟的请人编写的英文简历,从1200人中被录取了,那次,共录用了30人。在那儿,我干过保安、餐饮、行李员。当保安时,有一次,我把一个要去咖啡厅的老外指到了厕所,结果,被人家投诉。值班经理是菲律宾人,过来骂了我半天,我却一句也没听懂。这对我刺激挺大,我开始学英语,也为了能当上行李员多拿些小费。当上行李员后,我给李嘉诚、包玉刚的女儿等人拎过包。当我给李嘉诚拎着包,看着一大群人前呼后拥着他,走在人群最后的我觉得那真是气派。身为最下层的行李员,伺候的是最上层的客人,稍微敏感点的心,都能感受到反差和刺激:羡慕,妒忌,或是受到激励。
一天,一个旅游团住进饭店,一百多件行李需要我和另外一个人在30分钟之内送到十四个楼层不同的房间 。当我们气喘嘘嘘地把行李送完,爬到十四层楼道里去抽烟时,我看着楼下金鱼胡同里的一辆辆小轿车,说了一句‘早晚有一天有一辆车是属于我的!’这感觉是发自内心的。
有一次,父亲对我说他的一个朋友在王府饭店旁边开了一家中餐馆,让我帮着介绍客人过去。我就把一些外国客人介绍了过去,第一个月就介绍了两万多营业额。于是,中餐馆的老总请我过去当餐厅经理,每月600块钱工资,这跟王府行李员每月工资小费加起来3000多块钱相比,我还是舍不得。兼职吧!白天在饭馆从中午12点半干到晚上10点,然后再从墙头翻过去,到王府饭店上夜班,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,每天只睡三、四个小时。经常是刚刚在饭馆穿西装革履同外国客人交换名片、吃过饭,一个小时后,当我回到王府饭店,换上工作服同他打招呼‘先生,您好!’时,他却不屑一顾,我知道他不认识我。这样的落差这样的日子过了三个多月,我快坚持不下去了。
掀起怀旧风潮
我在那个餐馆只干了5个月就又失业了,餐馆的上级主管把它转卖给了别人,那是92年的春天。我和餐馆里出来的七、八个人闲着没事干,打了十几天的牌,我想这样下去不行,就偷偷去找门脸。最后,在民族饭店斜对面,找到一个因赔钱换了四个老板都没开成的小饭馆,我包了下来。我们拣来一些沙子、水泥和砖头,收拾了一通就开业了,叫民丰饺子馆。开张第一天只来了一个人,买了半斤饺子,4块钱。6个服务员全出来伺候这一个客人。吃完饺子那人抹抹嘴说:“虽说咱没去过五星级饭店,但五星级的服务也不会比你们好到哪儿去!”
我注意到,来这儿吃饭的人桌上都放着大哥大,大哥大那会儿还是有钱人的象征,这些人平常都是吃海鲜的主儿。一个客人对我说:“哥们儿,不瞒您说,好长时间没吃这么一顿饱饭了!”当时我就琢磨,为什么吃海鲜的人宁愿去吃一顿家家都能做、打小儿就吃的饺子呢?川式的,粤式的,淮扬的,东北的,中国的,外国的,各种风味的菜都风光过一时,可最后常听人说的却是:真想吃我妈做的什么粥,烙的什么饼!人在小时候的经历会给一生留下深刻的印象,吃也不例外。这时,我知道自己要开什么样的饭馆了,我要把饺子、炸酱面、烙饼 ,这些好吃的东西都搁在一家大的饭庄里。就这样,我又回到小时候待过的幼儿园,院里那棵大树和转椅还在,这里有我要找的感觉。我在院里拴了一只鹅,从农村搜罗来了井绳、辘轳、风箱之类的东西,还砌了口灶。备了擦皮鞋的,胡同口有免费的三轮车候着,我给这个饭庄起了个名字叫“忆苦思甜大杂院”。没想到很快就火了。
一股怀旧风开始弥散京城,北京街头陆陆续续出现了“老三届”、“黑土地”等饭馆。 我又开了“大年三十饺子城”等五、六家饭店。
茶,改变了我
一次偶然的约会,改变了我的生活。那个台湾的朋友回北京来小住,他在北京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。一天,他请我去他那儿喝茶。茶有什么好喝的?可当我见到他那套大老远从台湾背来的茶具,听着他讲解的茶经,喝着他为我沏的茶,不一样,就是不一样。没想到,这一喝,还真喝出点在中国文化里待了五千年的那个茶味儿,而且有一种不可改变的宿命的东西深入了骨髓,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。那年,我在地安门开了北京第一家茶艺馆,取名叫“五福茶艺馆”,寓意:康宁、富贵、好德、长寿、善终和知福、享福、惜福、造福、幸福。没想到茶艺馆生意冷冷清清,从忆苦思甜大杂院的大俗走到了五福茶艺馆的大雅,有些曲高和寡。但最关键的是没几个人知道茶艺馆是干什么的!有人进来问“有相声吗?有快板吗?有炒菜吗?那您这儿卖什么?”“有茶呵!”“那我还不如回家喝去!”我开始从闻香杯说起,我想把‘柴米油盐酱醋茶’的“茶”提升到‘琴棋书画诗曲茶’上的那个“茶”。但还是没人理解,没人来,没人来就赔钱。我在门口立了块牌子,上面写着: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内;酒后谢绝入内——有人说,本来就没多少人喝你的茶,还谢绝这谢绝那的。
第二年,我开了第二家茶艺馆。那段时间,我一个人捧着本茶经,把跟茶有关的一切研究了三年。再走出茶楼时,我变了。是茶,改变了我。
这时,生意开始有些变化,这变化首先是从客人身上开始的。一天,一群喝了酒说着粗话的人进了茶艺馆,我让一个茶艺小姐过去为他们服务,我要用静静的服务感染他们。20分钟后,这群人终于安静下来,走时,他们向我道了歉。我敢说,出了茶艺馆15分钟之内,他们是不会骂人的。人可以改变环境,但环境也可以影响人。谁会在王府饭店随地吐痰?茶艺馆虽说不是教化所,但他能让文明的人更文明,不文明的人暂时文明一些。如果一个城市多出100家茶艺馆,而另一个城市多出100家酒馆,晚上9点 以后,两地的治安肯定不一样。
今天,北京已经有 了400家茶艺馆,其中的四、五十家是我们帮开的,五福现在开了10家分店。茶艺馆70%以上是赢利的。为了倡导茶文化, 提倡把茶艺馆搬回家,我曾经和我爱人及服务员一起到各大商场去免费表演茶艺。五福成立了第一家茶艺表演队,代培茶艺小姐,搞茶叶茶具批发,提供开茶艺店的种种服务,并且,五福还同一家国企合作,成立了占地一万平方米的福丽特中国茶城。
在最困难的日子里,我总是这样鼓励我的员工:再微弱的光也是射向黑暗的一把利箭!你问我现在还问不问‘明年的今天我干什么呀?’问还是会问的,但不同的是,我清楚自己明天要干什么。因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愿意干一辈子的事儿,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。
夕阳站在地平线上的时候,我起身同段云松道别,走在三月傍晚的微风里,脑海中还在回味着段云松的那些‘怪论’。他曾不止一次说过:中国除了四大发明,还有茶!
老实说,上学时我不是个好学生,初中时,每到元旦前我就开始倒卖贺卡,我分给各年级的坏孩子每人十张贺卡,让他们到护士学校宿舍去卖,三毛钱进的卖一块,一百张就能赚七十块钱。上学时,我骑着三轮车带上五十条纱巾,等下课了就在校园里卖。初二时,爷爷去世了,父母回老家处理后事时,我就在家组织一帮孩子去卖莴笋,后来邻居告诉了我妈。当我在梦中喊着“瞧一瞧,看一看!”时,我爸过来从床底下翻出一杆秤来,他和我妈都很伤心。身为工程师和经济师的父母决不允许他们的儿子变成小贩子。看着他们的儿子整天烫着卷发,穿着喇叭裤,嘴里叼着烟卷儿,喝二锅头,交女朋友,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闲逛、打架斗殴,做小买卖,父母为此伤透了心。
放假时,我晚上在东四夜市卖油炸鹌鹑 ,白天帮着开小卖部的哥们儿卖烟,还骑着三轮车从塔院到紫竹院去进酱油、汽水。高三那年大年三十,我四点钟就起来,推着炉子、两百个碗和过桥米线到地坛庙会去卖,走了近三个小时才到,结果还让火把头发燎没了,卖了一百碗赚了九十块钱。
我知道了周末的韭菜比油菜好卖,香蕉见风就发黑。当然,这些都是从经验中得来的。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,每周六学校广播处分的名单里准有我,初三的模拟考试不及格,回家后,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躺在床上,我清楚地记得,当时,我妈站在那儿看着窗外,我知道她在哭。过了一会儿,她说了一句‘我真不知道明年的今天你能干什么!’,我一愣,深深地被刺痛了,一下子就坐了起来,我只说了一句话‘ 您放心吧!’。从那时起,我开始拼命地学习,我从全年级倒数第三名冲到了正数第十三名,考上了高中。爸妈高兴地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请了两大桌。后来,我学习又放松了,结果,大学没考上,我失学了。
总有一天有一辆车是属于我的
大学没考上,爸妈让我去他们的单位当个工人,我不去。当时,正赶上北京金朗饭店要开业需要人,凭着从朋友那儿现学的几句英语口语,我被录取了。又听说王府饭店在招人,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早晨五点就去排队抓号,还带了七八个小兄弟,让他们领七八个号,以减少竞争。结果,我靠着背熟的请人编写的英文简历,从1200人中被录取了,那次,共录用了30人。在那儿,我干过保安、餐饮、行李员。当保安时,有一次,我把一个要去咖啡厅的老外指到了厕所,结果,被人家投诉。值班经理是菲律宾人,过来骂了我半天,我却一句也没听懂。这对我刺激挺大,我开始学英语,也为了能当上行李员多拿些小费。当上行李员后,我给李嘉诚、包玉刚的女儿等人拎过包。当我给李嘉诚拎着包,看着一大群人前呼后拥着他,走在人群最后的我觉得那真是气派。身为最下层的行李员,伺候的是最上层的客人,稍微敏感点的心,都能感受到反差和刺激:羡慕,妒忌,或是受到激励。
一天,一个旅游团住进饭店,一百多件行李需要我和另外一个人在30分钟之内送到十四个楼层不同的房间 。当我们气喘嘘嘘地把行李送完,爬到十四层楼道里去抽烟时,我看着楼下金鱼胡同里的一辆辆小轿车,说了一句‘早晚有一天有一辆车是属于我的!’这感觉是发自内心的。
有一次,父亲对我说他的一个朋友在王府饭店旁边开了一家中餐馆,让我帮着介绍客人过去。我就把一些外国客人介绍了过去,第一个月就介绍了两万多营业额。于是,中餐馆的老总请我过去当餐厅经理,每月600块钱工资,这跟王府行李员每月工资小费加起来3000多块钱相比,我还是舍不得。兼职吧!白天在饭馆从中午12点半干到晚上10点,然后再从墙头翻过去,到王府饭店上夜班,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,每天只睡三、四个小时。经常是刚刚在饭馆穿西装革履同外国客人交换名片、吃过饭,一个小时后,当我回到王府饭店,换上工作服同他打招呼‘先生,您好!’时,他却不屑一顾,我知道他不认识我。这样的落差这样的日子过了三个多月,我快坚持不下去了。
掀起怀旧风潮
我在那个餐馆只干了5个月就又失业了,餐馆的上级主管把它转卖给了别人,那是92年的春天。我和餐馆里出来的七、八个人闲着没事干,打了十几天的牌,我想这样下去不行,就偷偷去找门脸。最后,在民族饭店斜对面,找到一个因赔钱换了四个老板都没开成的小饭馆,我包了下来。我们拣来一些沙子、水泥和砖头,收拾了一通就开业了,叫民丰饺子馆。开张第一天只来了一个人,买了半斤饺子,4块钱。6个服务员全出来伺候这一个客人。吃完饺子那人抹抹嘴说:“虽说咱没去过五星级饭店,但五星级的服务也不会比你们好到哪儿去!”
我注意到,来这儿吃饭的人桌上都放着大哥大,大哥大那会儿还是有钱人的象征,这些人平常都是吃海鲜的主儿。一个客人对我说:“哥们儿,不瞒您说,好长时间没吃这么一顿饱饭了!”当时我就琢磨,为什么吃海鲜的人宁愿去吃一顿家家都能做、打小儿就吃的饺子呢?川式的,粤式的,淮扬的,东北的,中国的,外国的,各种风味的菜都风光过一时,可最后常听人说的却是:真想吃我妈做的什么粥,烙的什么饼!人在小时候的经历会给一生留下深刻的印象,吃也不例外。这时,我知道自己要开什么样的饭馆了,我要把饺子、炸酱面、烙饼 ,这些好吃的东西都搁在一家大的饭庄里。就这样,我又回到小时候待过的幼儿园,院里那棵大树和转椅还在,这里有我要找的感觉。我在院里拴了一只鹅,从农村搜罗来了井绳、辘轳、风箱之类的东西,还砌了口灶。备了擦皮鞋的,胡同口有免费的三轮车候着,我给这个饭庄起了个名字叫“忆苦思甜大杂院”。没想到很快就火了。
一股怀旧风开始弥散京城,北京街头陆陆续续出现了“老三届”、“黑土地”等饭馆。 我又开了“大年三十饺子城”等五、六家饭店。
茶,改变了我
一次偶然的约会,改变了我的生活。那个台湾的朋友回北京来小住,他在北京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。一天,他请我去他那儿喝茶。茶有什么好喝的?可当我见到他那套大老远从台湾背来的茶具,听着他讲解的茶经,喝着他为我沏的茶,不一样,就是不一样。没想到,这一喝,还真喝出点在中国文化里待了五千年的那个茶味儿,而且有一种不可改变的宿命的东西深入了骨髓,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。那年,我在地安门开了北京第一家茶艺馆,取名叫“五福茶艺馆”,寓意:康宁、富贵、好德、长寿、善终和知福、享福、惜福、造福、幸福。没想到茶艺馆生意冷冷清清,从忆苦思甜大杂院的大俗走到了五福茶艺馆的大雅,有些曲高和寡。但最关键的是没几个人知道茶艺馆是干什么的!有人进来问“有相声吗?有快板吗?有炒菜吗?那您这儿卖什么?”“有茶呵!”“那我还不如回家喝去!”我开始从闻香杯说起,我想把‘柴米油盐酱醋茶’的“茶”提升到‘琴棋书画诗曲茶’上的那个“茶”。但还是没人理解,没人来,没人来就赔钱。我在门口立了块牌子,上面写着: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内;酒后谢绝入内——有人说,本来就没多少人喝你的茶,还谢绝这谢绝那的。
第二年,我开了第二家茶艺馆。那段时间,我一个人捧着本茶经,把跟茶有关的一切研究了三年。再走出茶楼时,我变了。是茶,改变了我。
这时,生意开始有些变化,这变化首先是从客人身上开始的。一天,一群喝了酒说着粗话的人进了茶艺馆,我让一个茶艺小姐过去为他们服务,我要用静静的服务感染他们。20分钟后,这群人终于安静下来,走时,他们向我道了歉。我敢说,出了茶艺馆15分钟之内,他们是不会骂人的。人可以改变环境,但环境也可以影响人。谁会在王府饭店随地吐痰?茶艺馆虽说不是教化所,但他能让文明的人更文明,不文明的人暂时文明一些。如果一个城市多出100家茶艺馆,而另一个城市多出100家酒馆,晚上9点 以后,两地的治安肯定不一样。
今天,北京已经有 了400家茶艺馆,其中的四、五十家是我们帮开的,五福现在开了10家分店。茶艺馆70%以上是赢利的。为了倡导茶文化, 提倡把茶艺馆搬回家,我曾经和我爱人及服务员一起到各大商场去免费表演茶艺。五福成立了第一家茶艺表演队,代培茶艺小姐,搞茶叶茶具批发,提供开茶艺店的种种服务,并且,五福还同一家国企合作,成立了占地一万平方米的福丽特中国茶城。
在最困难的日子里,我总是这样鼓励我的员工:再微弱的光也是射向黑暗的一把利箭!你问我现在还问不问‘明年的今天我干什么呀?’问还是会问的,但不同的是,我清楚自己明天要干什么。因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愿意干一辈子的事儿,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。
夕阳站在地平线上的时候,我起身同段云松道别,走在三月傍晚的微风里,脑海中还在回味着段云松的那些‘怪论’。他曾不止一次说过:中国除了四大发明,还有茶!
0
收藏
点击回复
- 共 0 条
- 全部留言
更多回复
- 你可能感兴趣的主题
- 回到顶部
Code © 2020-21 中华覃氏网 版权所有
鲁ICP备11005754号-1
联系QQ: 80353699 邮箱: 80353699@qq.com 电话联系:18661912830 免责声明:本站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,如涉及版权等问题,请您及时与我们联系,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删除及处理。 鲁公网安备 37021302000036号
鲁公网安备 37021302000036号























